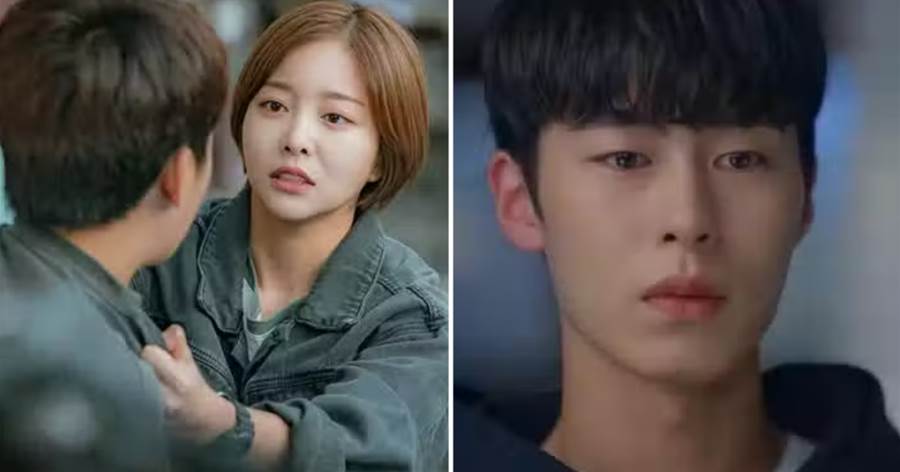同事說她女兒兩歲多的時候,有一次因為家庭瑣事和老公吵了起來,倆人越吵越兇,最后她老公吵不過她,上前一把推倒了她,看都沒看她一眼就出門了。同事也很生氣,抱著大哭不止的女兒就回了娘家,和父母講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,父母是既心疼又氣憤。等晚上吃晚飯的時候,老公來了,進門還沒開口說話,她爸上去就給她老公一個耳光,說我的女兒從小到大我還沒打過一下,你倒是敢打,夫妻倆吵架正常,但是作為男人你先動手就是不對。

她老公那晚表現得很好,對那一耳光沒說啥,紅著眼眶給同事道了歉,又握著她父母的手反復保證以后絕不動手,最后小心翼翼把她們母女接回了家。原以為風波就此平息,可日子久了,同事才發現丈夫把情緒都埋在了心里。
他依舊會按時接送女兒、分擔家務,唯獨對岳父母的態度悄然生變。以前周末還會主動提去看望老人,後來卻總以加班、孩子要上興趣班推脫;不得不去時,也是悶頭坐在角落刷手機,問他話只簡單「嗯」「哦」回應,連「爸」「媽」的稱呼都省略成了「您」。
有次女兒幼兒園布置家庭作業,要畫《最溫暖的家》。女兒用蠟筆涂了滿滿一頁:媽媽和自己在粉色房子里吃蛋糕,爺爺奶奶在院子里澆花,唯獨爸爸的位置畫了一團灰色的烏雲。同事看著畫鼻尖發酸,輕聲問女兒為什麼,七歲的孩子歪著頭說:「爸爸去外公家時,眼睛總是看著地板。」這話像根細針,扎得她心口生疼。

去年春節,兩家人難得聚在一起吃年夜飯。
飯桌上,父親特意開了珍藏多年的白酒,想和女婿碰杯。丈夫卻以開車為由端起果汁,父親舉著酒杯的手僵在半空,最后自嘲般一飲而盡。飯后母親拉著女婿說要學用智能手機,丈夫教到一半,借口女兒作業沒寫完匆匆告辭。看著父母站在樓道里目送他們離開的身影,白發在寒風中凌亂,同事突然發現,父親的背不知何時佝僂得厲害,母親眼角的皺紋里滿是失落。

夜深人靜時,同事翻出七年前丈夫手寫的保證書,紙張邊緣已經泛黃。她既理解父親當年護女心切,也明白丈夫被當眾羞辱的難堪。如今女兒常問「為什麼爸爸不和外公下棋」,老人每次打電話都要問「女婿最近忙不忙」,話里話外都是想修補關系的試探。她對著鏡子嘆氣,眼角不知何時添了細紋,當年沖動回娘家的決定,像顆扎進生活的刺,拔出來會疼,留著又硌得慌。

她嘗試過私下和丈夫溝通,可話到嘴邊又咽下。丈夫總說「都過去了」,卻在聽到「回娘家」三個字時下意識皺眉;她也想過讓父母主動示好,可想起父親倔強的脾氣,母親偷偷抹淚的模樣,又開不了口。無數個深夜,她躺在床上聽著丈夫均勻的呼吸聲,望著天花板發呆:難道真要年邁的父親先低頭道歉?還是該帶著丈夫主動破冰?可那些沉默里積壓的情緒,又該怎麼化解呢?窗外的月光灑進來,照著她輾轉反側的身影,而這個橫亙在兩家人之間的結,依然緊緊纏繞著,找不到解開的線頭。